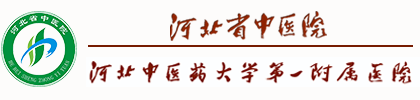
肉类食物:当癌症遇见红色肉类
建议
将红色肉类(牛肉、羊肉、猪肉)的摄取量限制在每周500g左右,进餐时选择以鱼类、蛋类及植物蛋白为主的食物来替代红色肉类。
来源: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
法语中的viande (肉类)一词是由拉丁语“vivenda”(即生活、生命之意)衍生而来。“Viande”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固体食物的统称,既可指代面包、蔬菜、坚果,又可指代以动物或鱼肉为主的正餐。例如,在路易十四位于凡尔赛宫的晚宴中,当“Messieurs, à la viande du roi”(先生们,这是国王赏赐的盛宴)这句话响起时,viande一词就不仅仅指代动物肉,而更多的是指太阳王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珍馐。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开始用“viande”来特指猪、牛、禽类等可食用动物。其在含义上的转变很好地体现出这些食物对于人类固有的吸引力,同样也体现出这些食物在人类饮食中普遍性。
许多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肉类为何在人类饮食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主要原因却非常浅显:大多数人喜爱肉食是因为肉类味道非常可口。虽然烹调生肉毫无情趣可言,但在烹调的过程中,肉类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这些化学反应会产生成千上万极其芳香的分子,从2-甲基-3-呋喃硫醇到3-巯基-2-戊酮,并且还包括数以百计由肉类糖分及蛋白质间反应所生成的挥发性物质。在这些分子中,有些挥发出的香味会让人想起水果的味道,有些则是蘑菇或坚果的味道,然而经过大脑的整合,这些分子会产生一种新的香味,一种无法在自然界中找到,仅在烹调时才有的香味,即烹饪肉菜时所散发出的无与伦比的香味。
肉类食物之所以美味,并不仅仅如此。烹饪肉类除了会产生独特的香味外,还会释放出两种能够被味蕾中味觉受体识别到的分子,即谷氨酸和肌苷酸分子。这些味觉受体能够专门识别umami(鲜味)这种味道(umami一词由日语中的umai、mi二词组成,前者表示美味,后者表示味道),并将这种味道传输给大脑,让大脑意识到富含蛋白质食物的存在,从而激活大脑中的快乐中枢以及奖励中枢,使得肉类菜肴令人食指大动。而拒绝肉类佳肴对人类而言则十分困难——包裹胎儿的羊水中富含谷氨酸,这就意味着自人类拥有生命那天起,大脑的快乐中枢就开始受到这种物质的刺激。
(标题, p. 78) 左图为人类大脑,右图为黑猩猩的大脑
从草食动物到杂食动物
人类对于肉类食物的偏爱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大约叁佰万年前,我们的远古祖先能人(Homo habilis)就抛弃了大猩猩那种几乎只吃植物的传统饮食习惯,开始在植物中填加肉类食物,这些肉来自食肉动物留下的食物残骸。能人通过这种方式尝到了动物肉的滋味,并转变为猎手。对于能人来讲,这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因为他们拥有较小的体型(约1.2米,40千克),缺少较快的速度,也没有爪子及锋利的牙齿,这些缺点使他们无法成为合格的猎手,更不要说是捕食者!但这次转变却对人类后世的进化起到了非同凡响的作用。因为肉类属于高热量食物,并富含必需营养物质,所以其能够提供大脑发育所必需的额外能量。因此,食用肉类使人类的脑容量得到了惊人的发展 (详见方格内容)。能人通过这种鲁莽的行为,从通过捡拾才可获得肉类的弱者角色,转变为了可怕的捕食者角色,他们通过智慧从肉类中汲取了宝贵的能量。然而,这些新的饮食习惯并没有将我们变成肉食动物!虽然我们享用并消化肉类食物,但我们既不在解剖结构上(牙齿、颌骨及胃)与依靠肉类为生的肉食动物相似,也不在生理机能上(尿酸代谢)与其相似。从生理层面来看,人类实际上是以植物源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生物,但从文化层面上看,人类习惯于多元化饮食,习惯于在此类食物中添加多种肉源性食物。
强健大脑
尽管人类大脑仅占体重的2%,却独自消耗着静息状态下机体20%的能量。处于警觉状态下的大脑对于能量的需求则更为巨大,每十亿个神经细胞需要约6卡路里能量。因为人类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发生了惊人的发展,因此人类的远古祖先不得不将他们每天的卡路里摄取量增加大约700卡。
毫无疑问,如果原始人类还固守着大猩猩的草食性饮食习惯,那这种程度的能量需求是非常难以满足的;如果让原始人类仅靠吃周边的植物性食物来满足这种额外的能量需求,那一天需进食9小时以上,考虑到收集到足够食物所需要的时间,这种方式显然不可能达到开发大脑的效果。
食用肉类使这种能量需求问题得到解决,并促进了人类大脑的进化。一方面,由于肉类是高热量食物并富含大量必需维生素及矿物质,其能够满足功能增强后的大脑运行所需的最基本能量需求。但是,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智商的提高使原始人类能够制作并使用工具,原来那些难以获取的高能量肉类及食物,在工具的帮助下,变得较为容易获取。例如骨髓或大脑,它们为神经元发展提供所必须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随着智商的进步,人类能够熟练地使用火,并开始蒸煮食物,这使得食物更容易被消化,进而增加了能量及必需营养物质的摄入量。质量更高的饮食有助于缩短婴幼儿哺乳期,从而提高了女性的平均生育数量,这意味着人口数量的飞快增长。
红色肉类与白色肉类
我们今天所食用的肉类与史前时代那种在荒野生存中所获得的肉类是非常不同的,是早期文明不遗余力驯化野生动物的成果。不论是一万年前土耳其东南部的绵羊,山羊和牛,还是八千年前土耳其和亚洲的猪,亦或是八千年前东南亚的鸡,所有这些动物的存在使得人类可以依赖于肉类的正常供应得以生存,而同时人类的生活也更为安逸。值得注意的是,一万年后的今天,构成人类饮食主力军的,仍然是这些动物肉类,在加拿大,鸡肉、牛肉及猪肉占据着每年肉类食用量的90%。
所有的肉类食物,无论源自牛、羊、猪或是禽类,其肌肉都具有相似的结构,即由肌纤维、动物脂肪及结缔组织构成。然而,这些成分在肌肉的构成比中,却有着显著的差异,尤其是其脂肪含量:相同重量的肉类,其脂肪含量可从禽类肉中的不到1%到牛肉中地大于30%。这些肉中不同的脂肪含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肉类的不同口味,特别是位于肌纤维间的脂肪含量(例如被牛肉爱好者们高度评价的大理石纹牛肉,其实这些大理石纹就是这种肌内脂肪)。但是,这些不同种类的肉所具有的最明显可视性差距则是它们的颜色:牛肉、猪肉、羊肉及马肉这些都被称之为红色肉类,而禽类如肌肉或火鸡肉则是白色肉类。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肉在颜色上的不同呢?乍一看,这貌似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这个问题对于理解肉类对于人体健康的各种影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红色肉类
肉之所以是红色,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是因为肉里含有血液。红色其实源自这种肉类的高肌红蛋白含量;肌红蛋白是一种通过与血红素辅基(一种含铁的辅因子)相互作用从而与氧气相结合的蛋白。这种血红素铁使肌红蛋白能够在肌肉中储存氧气,从而供养肌肉收缩所需要的高强度代谢活动。那些需长时间保持工作状态的肌肉,例如帮助保持平衡或行走的肌肉,则需要更多的氧气,因此,这部分肌肉往往肌红蛋白含量更高(牛肉中1-2%,猪肉中0.2%)。在生性好动的野生动物中(野牛、麋鹿),有时肌红蛋白的含量甚至高到肉看起来都成了黑色!
肌红蛋白与氧气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变化导致了红色肉类在储存或烹饪时颜色上的变化。例如,当温度达到约华氏140度(摄氏60度)时,肌红蛋白中的铁失去一个电子(也就是说铁被氧化了),之后铁原子便无法再与氧气结合,使得烹调过的肉类呈现特有的褐色。
肉类的颜色也可以通过化学作用改变。在一些国家,人们有时会将少量一氧化碳(CO)加到肉中,这样既可防止肌红蛋白氧化又可让袋装肉类的红色看起来更加吸引人。但是,这种红色却能在肉类变质后依旧惹眼讨喜,这便增加了食物中毒的风险。另一个人工改变肉类颜色的例子则是“粉红肉渣”,一种牛肉加工过程中剩余的边角料做成的肉泥并添加氨气以除菌。在这种添加氨气后的碱性条件下,肉类会具有一种特别倒人胃口的粉红色,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美国政府批准粉红肉渣的商业性使用,即成为碎牛肉或加工肉的填充料,就像冷切肉一样。
加工肉类
以肉制品的形式来处理肉可以追溯到古代,这种技术在制冷技术发明前可以延长肉类的保质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肉类的营养价值并不仅仅吸引人类;微生物同样喜欢肉类并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其腐坏从而无法为人类所食用。例如,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他们将血或充分切碎的肉块填塞至动物的内脏或胃里,并将盐、调料及香料作为防腐剂加入其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使用大量的盐,因为盐能使肉局部脱水,从而减少潮湿的环境所造成的病菌增值扩散。实际上,英文中“sausage”(香肠)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salsus”,即“咸的、含盐的”意思。
早期的专业屠夫们,包括相传是血肠创造者的希腊大厨Aphtonite,都并不知道他们所用的盐里含有硝石(硝酸钾)这种成分。这一举动是意外的惊喜,因为这些硝酸盐属于强力抗菌剂,这种特性必然已经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使他们免受多种潜在的致命性中毒物质的伤害,如肉毒梭状芽胞杆菌。硝酸盐的另一优势在于其可以降解为亚硝酸盐并能进一步降解为一氧化氮(NO),一氧化氮能够与肌红蛋白相结合,进而将肉变为桃红色并使其能够储存数个星期而不腐坏。
白色肉类
白肉是由所谓的“快”肌纤维所组成,快肌纤维主要参与机体短时间内的无氧运动。因此,这些肌肉并不含有或仅含有非常少量的肌红蛋白,其能量则主要来源于糖原,一种作为糖类仓库的葡萄糖聚合物,这种葡萄糖聚合物为肌肉收缩提供了所需的“燃料”。像鸡和火鸡这样的禽类几乎不飞行,并且已经习惯于运用它们的翅膀进行快速但距离较短的移动,因此,它们的胸肌中几乎完全不含有肌红蛋白。另一方面,这些禽类动物行走较多,所以它们的大腿需要更多的氧气来维持它们的速度,因此它们大腿肌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较高,并且看起来颜色较暗(褐色)。
肉食性动物的风险
尽管肉类曾经是一种奢侈的食物,一度十分昂贵,仅在重要场合食用,但随着现代社会大规模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肉类食物具有了广泛的可用性和低廉的价格这两个特点,从而使其在现代饮食中变得十分常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肉类食物的消耗量已呈爆炸性发展态势,但印度则是个例外,出于宗教的原因,这个国家有40%左右的居民,根本不吃或不常吃肉。例如,在中东或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人们过去习惯于吃少量的肉,但是现在则不然,人们对于肉类食物的摄入量已是原来的两倍,有时甚至达到了原来的五倍,而这一趋势似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会一直持续下去。即便如此,工业化国家依旧是这个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头羊,这些国家的人均肉类食物摄取量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两倍。
很久以前人们便知道高比重红肉及低比重植物性食物的饮食方式加上体重过重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增加了大肠癌的患病风险。这种生活方式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惊人的,像北美或欧洲这种工业化国家,其人民结肠癌的发病率是印度或位于中东及非洲国家人民的5到30倍。
日本向大家展示了一个惊人的例子,那就是一个社会的工业化能够讯速地影响癌症发病率。二战以前,在日本人悠久的饮食传统中,海鲜及豆类植物,如大豆,一直都占据着很大的比重,但此后,日本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肉类食物的摄入量激增(原有水平的700%),红肉摄入量的增长尤为显著。另外,在日本,超重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30年前,日本的大肠癌发病率在世界上仍属于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然而生活方式的明显改变导致日本的发病率增加400%,目前其发病率已与欧洲及美洲的一些国家相同。并且,发病率的激增在年轻人群中尤为凸显,主要体现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人群中,这表明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会导致癌前病变的快速形成并极大加速了癌变的发展过程。
红肉和加工肉类经常被看作是大肠癌在工业化国家的高发病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大量摄入红肉或加工肉类的人群罹患大肠癌的风险较仅少量进食这些食物的人群增加了约30%。日均摄入50g红肉或加工肉类,患癌风险将增加10%左右,而每日摄取红肉或加工肉类超过120g者,其患大肠癌风险最高。这种影响仅在摄取红肉的情况下发生;摄入鸡肉或鱼肉对患癌风险并无影响。
红肉不仅会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还对人类的寿命有不利影响。一项涉及50万人的大样本研究表明进食红肉及肉制品与死亡率呈线性递增关系,每天吃160g红肉或肉制品的人,其早亡风险较常人高出50%。后续分析表明,这种不利影响主要归因于加工肉类的摄入(熏肉、香肠、腊肠、火腿……)。摄入此类食物最多的人群,其死亡率可增长20%-40%。而每日摄入新鲜红肉(牛肉、猪肉、羊肉)最多的人群,与平常摄入很少或根本不摄入此类食物的人群相比,其早亡风险则增加了13%。
致癌物质的生成
进食过多红肉所带来的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反映了红肉的高热量密度,同样也反映了在烹饪或保存时,红肉所发生的主要生物化学变化。首先,人类需要承认在进化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肉中的高热量物质已在当今食物过剩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进食大量红肉更易导致超重或肥胖。其次,一些研究表明,大量摄入红肉的人群,其患II型糖尿病的风险更高,因此更易导致超重。由于肥胖是导致某些癌症(尤其是大肠癌)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进食过量红肉所导致的热量过剩则肯定会增加大肠癌的患病风险。
此外,人们认为某些因素也可能导致癌症在摄入大量红色肉类以及加工肉制品的人群中进行扩散。例如,这些食物中所含的血红素铁会产生自由基并促进亚硝氨基化合物的形成,而这些亚硝氨基化合物则有着十分危险的特性,即能随机的与人类的遗传物质相结合,进而引起人类DNA的突变。因为肉制品既是这些致癌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也含有能够转变为亚硝胺类物质的亚硝酸盐,所以这些分子很可能会导致加工肉类对世界部分地区人们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烹饪红肉可能也会加重其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在高温状态下(大于摄氏200度或大于华氏400度),肌肉细胞中出现的大量肌酸会与蛋白质中的氨基酸产生化学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叫作杂环胺(HCAs)的物质,这种杂环胺也具有与人类DNA相结合并诱导癌症发生的能力。
这些复杂的分子很容易出现:肉越焦则杂环胺的含量越高!以牛肉为例,烹调时间较短时(五分熟),其杂环胺含量较低,但当牛肉全熟时,这种致癌物质的含量较之前则翻了三倍,而像熏肉这类肉制品在制作过程中杂环胺含量则更高。人类已在高温烹调的肉类中发现了15种左右的致癌分子。另外,一些研究也显示大量摄入烧焦的肉类会增加结肠癌、胰腺癌及前列腺癌的患病风险。
但是,将肉浸入初榨橄榄油中,并在橄榄油中加入大蒜及柠檬汁或百里香、迷迭香这种香料,即可轻松消除掉肉中含有的这些分子。这种腌泡汁也可以减少70%丙二醛的生成,丙二醛是动物脂肪的副产物,能够增加患心脏疾病的风险。含有如红烧酱汁或姜黄的腌泡汁则更为“亚洲化”,这种腌泡汁可以减少三分之一杂环胺的生成,而饭店中的烧烤调料则会制造出三倍于正常水平的杂环胺。即便工作繁忙的人也可以将杂环胺的生成减半,他们仅仅需要在烹饪碎牛肉前添加姜黄(0.2%)或相关香料(凹唇姜、高良姜)即可。减少烹调致癌物的方法无穷无尽,而其中一种则来源于加勒比人古老的烹调传统,他们习惯于在烤肉(barbacòa)前将肉在香料以及姜黄中浸泡,而这就是如今烤肉的前身。
今天的肉类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使红色肉类生产出现爆发式增长,而这种增长导致了肉类成分的重要变化。肉用牛这种反刍动物通常以三叶草和苜蓿这些植物为食,但这些动物现在则是通过玉米和大豆来催肥的,通过摄入这些食物来加速它们的生长以便尽快宰杀。牛在饮食上的这些变化对于牛肉的成分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玉米是淀粉的来源之一进而也是糖类的来源之一,而这种糖能够被动物转化为脂肪。通过这种喂养方式获得的牛肉其脂肪含量大约是草饲牛肉脂肪含量的两倍,这些脂肪就堆积在肌肉中。因此,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牛肉切片中都能找到“大理石纹”,这些纹路向我们表明了哪些牛的生长是通过人工喂养大量糖类而加速完成的。
这种饮食方式对于肉类中必要的促炎Ω6及抗炎Ω3脂肪同样有着重要影响。玉米中并没有Ω3,所以,进食这种谷物的动物与草饲动物相比,其抗炎脂肪的含量仅为后者的1/3。而对于Ω6脂肪来说,则恰恰相反,通过喂食玉米而获得的牛肉,其促炎脂肪含量是草饲牛肉的两倍。因此,牛饮食上的改变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现在的牛肉其Ω6与Ω3比值约为13,而经过传统方式饲养得到的牛肉,其比值则是2。这一差异十分显著,因为西方饮食中Ω6脂肪的含量比Ω3脂肪含量多10到30倍,这会导致体内炎性环境的形成,这种环境可以促使许多慢性疾病发病。关于癌症,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阿根廷,进食在牧场长大的牛的牛肉(草饲牛肉)是彰显公民身份的一种方式,尽管其在牛肉方面的摄入量是加拿大方面的两倍(阿根廷:人均58公斤,加拿大:人均27公斤),但其大肠癌发病率却仅为加拿大大肠癌发病率的1/2。大家都说人类吃什么就像什么,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们同样也像我们所吃食物的饲料一样。与红肉制品相关的畜牧业极端产业化发展方式和过多摄入这些食物很可能共同影响了人类的健康。
因此,过量摄入红肉及加工肉类而危害健康的原因有很多,可从肉类含有的高热量物质,到烹调或储存时产生的致癌化合物,再到非正常指标的低抗炎Ω3脂肪酸含量。人们需要牢记的一点是,有研究表明大量吃肉的人往往吃的植物性食物较少,进而失去了他们珍贵的抗癌盟友。例如,研究已经表明,绿色蔬菜如菠菜能够通过降低毒性分子的致癌作用而扭转肉类中血红素铁或杂环胺所造成的危害。
不容忽视的间接伤害
每年有超过530亿只动物被宰杀来满足人类的食用需要,显而易见,畜牧业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温室气体的产生,为生产出足够多饲养动物的谷物而导致的耕地和水的大规模使用,以及将动物囚禁在十分有限的空间里,这些都是畜牧业集约化的后果,而这些后果能导致地球生态系统在中长期发生剧变。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是因大规模畜牧业而导致的间接伤害,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人们注意到服用过抗生素的动物长得更快体型更大,这样不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也可降低销售价格。起初,抗生素是作为药物为患病动物治病所用,但现在已成为畜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供以健康动物服用。在美国,据估算每公斤肉类和蛋类的产出需使用约300毫克的抗生素,而这个国家的抗生素有80%是用在了牲畜身上。用在健康牲畜身上的抗生素要多于用在患病的人类身上,这是件多么令人不安的事儿。
细菌适应不良环境的能力无与伦比。尽管抗生素可清除掉大量细菌,但这些药物的持续使用则会导致一些细菌产生耐药性。所以,不恰当以及过度使用抗生素会为动物体内耐药菌新菌株的出现创造条件,不仅如此,这种抗药性随后会传给致人感染疾病的细菌上。
这种情况十分令人担忧,我们无法坐以待毙。正是由于青霉素及其后上百种新型抗生素的出现,才使我们人类的寿命在20世纪有了明显延长。在抗生素出现以前,由于当时治疗手段的无效性,如若感染了诸如肺结核、肺炎或严重腹泻等传染病,人们常常会过早的离世。这样看来,抗生素绝对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因为抗生素的存在使我们战胜了严重的传染病并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现在,经药厂研发生产出来的新型抗生素变得越来越少,如果我们不能谨慎地用药并且严格限制动物用药,那么早晚有一天,在面对细菌性疾病时,我们现有的治疗武器将无以应战。近年来耐药结核病已呈爆发趋势,仅在2012年就令17万人丧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明确指出17种对于抗生素存在耐药性的微生物,而这些微生物每年能够造成2万3千人死亡。
用什么来替代它?
大多数公共卫生机构建议成年人每日摄取二至三份肉类食物或肉类替代品,相当于160-240克蛋白质。将豆类、坚果和蛋类这些即健康又高质量的食物称作肉类的“替代品”着实有些不太公平,因为它们就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吃进去的每一口都跟肉类食物中的优质蛋白一样富有营养。而且这些替代食物确实可以挽救生命。无论是鱼肉、禽类肉、坚果还是豆类,这些蛋白质来源作为红肉的替代食物可以迅速降低因红肉引起的早亡率的上升趋势,将早亡风险从20%降到7%。人类同样不应忘记那些富含脂肪的鱼类,如鲭鱼、沙丁鱼和鲑鱼,这些鱼类是长链Ω3脂肪酸的主要来源,也是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六碳六烯酸(DHA)的主要来源,这些物质对于保持组织内抗炎抗癌环境有所帮助。
我们不能因为美味的肉类食物就忘记了当下我们所消耗的动物肉类要远远超过其推荐摄入量,我们也同样不能忘记膳食蛋白质来源多样化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植物性食物在膳食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与主要进食植物来源的蛋白质相比,那些整天啃食动物来源的蛋白质(肉类、乳制品)的人群,其死亡风险是前者的四倍。
上一篇:癌症与蔬菜
下一篇:为银屑病患者进行宣传教育